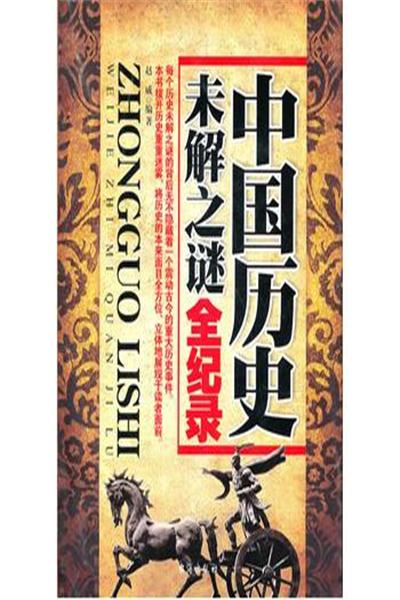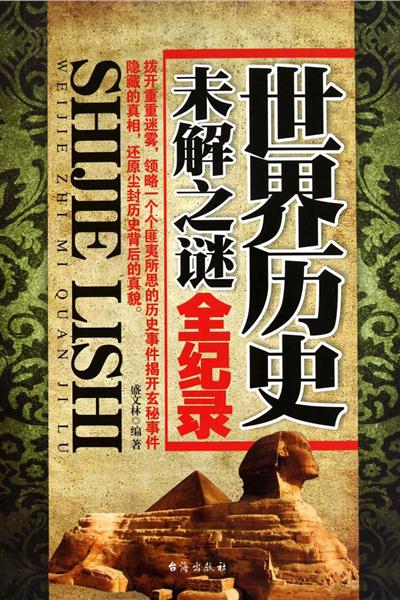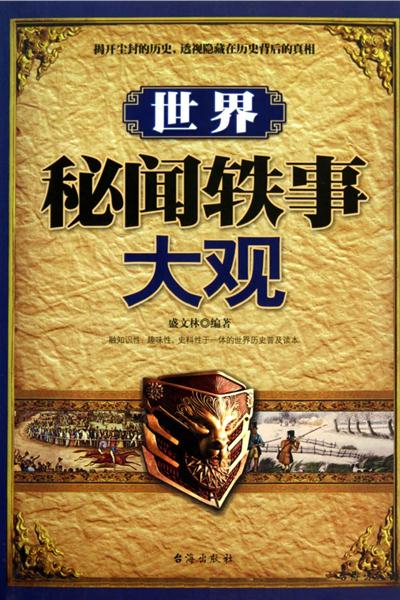鲁斯主教并不是普通的传教士。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即将从这份使他获得了地位上的自信的工作中退居二线。他的私人朋友基本都是政府官员,包括蒋委员长及他的夫人。鲁斯主教的思想开明,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共产党领导人、国民党领袖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不论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践行着基督教的教义,对中国领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事风格有着很大影响力。
有一天,公共关系副部长霍灵顿·唐医生过来找我,带我去与蒋委员长及其夫人会面。霍灵顿正如新闻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亲切。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国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被蒋委员长当做一位可以信任的朋友,并且在1937年出版了委员长的传记。
我们横渡长江后到达了武昌,开车到了一座被他们夫妻当做居所的装饰简单的公馆外。自从1929年国父孙中山的葬礼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好奇经历过岁月的洗礼后,他们是否还似当初。
干练果断的上楼声在屋外响起,蒋夫人跟在站得笔挺的蒋委员长后面进了屋。
蒋夫人迷人的魅力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那并不是幼稚的年轻人的魅力,而是知性成熟的魅力。不过更多的是由心而生的一种成熟的落落大方,以及要服务人民、成为他们引路人的使命感。
他们二位都兴奋地欢迎了我的到来,蒋夫人随后在铺了一张地图的桌子旁坐下。蒋委员长直到有他的夫人扶着才坐了下来。蒋夫人转过身跟我解释道:“委员长在西安后背受了伤,这些年一直饱受折磨,不能站的太久。”
我将他视为在过去几十年中掌控着中国命运的男人。同我上一次见他时相比,他似乎苍老了许多,短发也变白了,但是比往日多了一丝沉稳和自信,也更加老练和成熟。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在他眼里,我看到的是智慧、忠诚和倔强的决心。
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我向他讲述了我在北方的经历,回答了他们犀利的问题。我向委员长表达了我对八路军领导人的绝对信心,描述了他们正在敌后地区建立代表政府的进度。当我提到五台地区的人民一致抗日的意愿非常强烈,军民合作良好时,蒋委员长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
“我相信,”我回答道,“这是基于他们现在正处于日军包围的这一事实,他们时刻都面临着危险境况迫使他们放弃个人利益而谋求集体利益。更深远的层次上,他们是受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领导所影响。”
委员长的脸上一时看不出对于这一想法的反应。毫不夸张地说,他的面部表情永远难以捉摸。他威严的沉着镇定是他成功成为领袖的一大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自信,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嗅觉、信守诺言也养成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他的政治倾向难以预测,管理方式也让人摸不到头脑,但是私下里大家都心知肚明,蒋委员长打心眼里偏向于执行自己所处政治集团的决策。
结束时,他们起身要走。我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个名,他和善地默许了。他用的铅笔一头是红铅一头是蓝铅。签字时委员长泰然自若,红的那头落下,飞快地在纸上滑了几下然后又用蓝笔写。这个字签得争分夺秒,但是意味着很多。
回到了汉口,霍灵顿·唐带着我去行政院长暨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家里吃午饭。在那我们看到了兰德尔·古尔德——一位言辞恳切的编辑,就职于上海唯一一家美国报社。兰德尔·古尔德坚持发表事件的真相,也因此收到了日军恐怖分子的炸弹威胁。
孔博士是我的另外一位老朋友。他的外表看着有点胖,留着短短的胡子,戴着眼镜。在美国的大学接受教育后回到了中国,现在山西领导奥柏林教会学院。孔医生跟宋氏三姐妹里的大姐宋霭龄结了婚,为未来进军政界和商业投资奠定了基础。自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他一直担任实业部长及财政部长,现在又担任了相当于共和国首相的职务。不过最令他自豪的可能是他显贵的出身了,即外国人无人不知的孔夫子——孔子的直系后裔。
那天在孔博士的桌子旁坐着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一位高大健壮、行为和善、善于演讲的男人。还有一位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以及国民党委员会的前任高官陈公博先生,对于蒋委员长现在推行的政策他颇有微词。一年间,他加入了汪精卫的队伍,试图在日本统区下建立傀儡政府。
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介石任正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是这些人里行为举止最怪异的人。他的身高超过了六英尺,臀部肥大。他为成为人民的领袖而感到自豪。早年间还在国民军时,他就以不拘小节闻名全军,或是同士兵一同行军,或是坐在卡车司机旁的副驾驶座位上。1930年时他就军队编制问题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还一度联合阎锡山将军发动了反蒋战争,当然最后以失败收了场。但是他的名字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还是很响亮,而且他的爱国心远远超于对抗日战争的热情。
何应钦将军有点难以琢磨。他的身材不高,戴着眼镜,平静温和,笑容可掬。几年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曾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陆军将领,他频繁地被派遣去解决紧急事件就是证据。1936年蒋介石滞留在西安时,一些目前处于保密状态不便公之于众的事态的发展改变了这个曾经亲密的联盟。表面上他并没有丧失任何的信心,也已经接受了不再担任任何重要的指挥职位的现实。
当我跟这些管理着民族事务的人们聊天时,我无法否认这与我同精力充沛又自律的八路军在一起生活时身体感官上的强烈对比。两支队伍的领袖都同样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都办着代表各自思想的学校。不只是这场战争中日本战败所要接受的惩罚,还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如何在战后发展,都将取决于两党能否制定一个双方都接受的方案。如果我对广大人民百姓的脾性了解的正确无误,鉴于这个民族已经将民主主义融进了他们的骨血,那么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将会成为可行的方案,在由人民管理的同时服务于人民。
大使先生的座上宾通常都是从香港飞来一睹中国战时首都的。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约翰·冈瑟了。有天他携同他迷人的妻子来吃午饭,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来了解来自欧洲的第一手消息。谈话也并不是单向的,冈瑟用他乐天的性格活跃了我们的气氛,不停地询问着战争的进度。这些问题都直指关键部分,通过这些问题可以看出约翰对于东方国家的深刻理解。每隔四五个问题,冈瑟夫人就会提出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我们总结,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成为一支水平颇高的新闻报道团队。
另一个在汉口工作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周恩来,他是旧中国政府的后人,穿衣说话都非常文雅,但是他有着不次于我在北方见过的任何一个人的自我约束能力。周恩来有着中等的身材和儒雅的作风,聆听别人说话时总是带着一种超脱的信以为真的感觉。他有着中国首屈一指的天才般的头脑,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中的意见也举足轻重。在国民党成立初期,他就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于1927年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工人起义。
一天晚上当我正在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人吃晚饭时,艾格尼丝对于外国记者没有在报纸上报道事实的真相愤愤不平。周恩来久久地凝视着空气,没有注意打到她在发表的长篇大论。不久他端坐起来,用他独有的习惯性姿势,手捧着下巴,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平静地评论道:“如果记者能够丝毫不差地记录当下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快到三月下旬时我又准备出发了。在了解了游击队的行动特点之后,我希望去看看徐州前线上的其他冲突。J·L·黄将军在南京时慷慨相助,当我从京口铁路和陇海铁路的枢纽站乘车前往郑州时,他帮助我提供了必要的身份证件。如果这儿的军官能允许的话,我希望可以停留一两天观察他们行动和决策的焦点问题。
桑福德·埃尔斯医生在郑州管理着浸礼会教会医院,他的家也变成了居无定所的记者和武官的临时住所。即便我只是一个在深夜造访的陌生人,他们还是起了身查看到底是谁搭乘了这么晚的火车。
因为医生对东线转移过来的伤患有一套很见疗效的治疗方法,他的普通病人的数额不断上升到了医院难以招架的程度。当有人满脸忧愁地前来看病时,我总与他一同坐在桌前,他从不会因为太忙而忽略倾听任何一个中国病人叙述自己的病情。有时还没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起身到门口迎接病人的到来。
一天晚上正在吃饭闲聊时,有消息说一辆从徐州开出、带着上千受伤士兵的火车驶达了郑州。中国军队的外科医生担心埃尔斯医生是否会提供帮助来为他们做检查,是否会对这些需要立即处理的病例区别对待。
埃尔斯医生把他的团队成员集合起来赶往火车站。这支小分队包括麦克克鲁尔医生、英国人汉克,还有新西兰人特沃。
伤员们都躺在货车、煤车和乘客休息椅上。他们离开前线只有三天的时间。虽然伤员们第一时间已经接受了急救,但是很多人还是感染了坏疽。大概有五十个坏疽病人被转送到了医院并在急救室度过了那个夜晚。
战士们身上的枪伤是他们又一次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日军机关枪攻势的一个铁证。上海的大部分士兵的伤口都是由炸弹碎片造成的,这意味着中国军队正在进行攻击。
时任正面战场指挥的程潜将军在郑州的指挥部亲切地接待了我,告诉我李宗仁将军将非常欢迎我去徐州前线。他的个子很高,行动很缓慢,五十七岁,留着小刷子一般的胡子,最近刚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第二天他把我送上了东去的火车,同行的还有作为翻译的包世天(音译)先生。